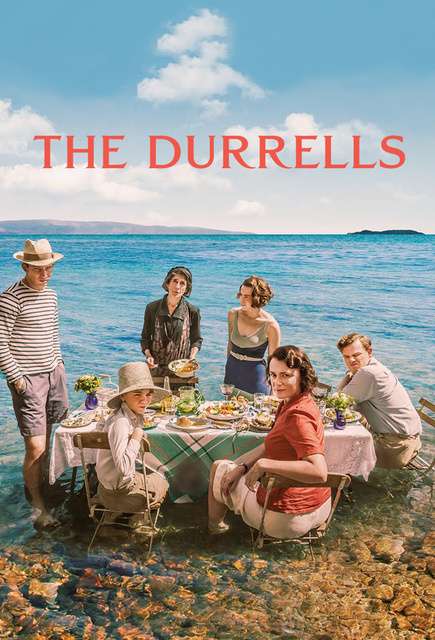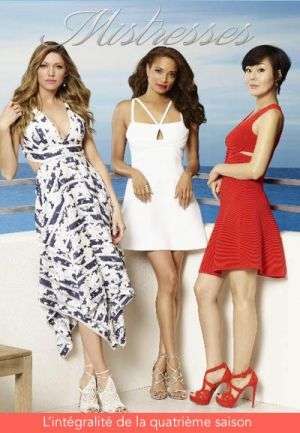剪不断理还乱的母女情仇-孟若《年少友人》

有关母女恩仇的电影,记忆中柏格曼执导的《秋光奏鸣曲》以及梅莉史翠普与凤凰女茱莉亚罗勃兹主演的《八月心风暴》最让人印象深刻。由于我跟母亲的感情亲密,因此很难想像母女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交织,更遑论母女对峙狂啸、尖酸刻薄的歇斯底里,每每看得我冷汗直流、呼吸窘迫。
昨晚读艾莉丝・孟若近60岁时写的短篇《年少友人》,一股熟悉的凉意从背脊爬上来。同样谈母女爱恨,孟若写得极冷,丝丝缕缕隐藏在含蓄的笔触中。故事的结构安排像俄罗斯娃娃,一个大故事包复着几个小故事,当答案揭晓,发现里头爬满了蚤子。
孟若的作品不好读,情节少、独白多、蹊跷多,不是那种看一遍就可以轻轻放下的小说。例如这篇《年少友人》,读的时候有些地方觉得古怪,有几个关键句很难跳开,但孟若又不把话挑明,她要让读者自己去回游思考,走进去再走出来。写小事,举重若轻;写人心,百转千回,精致的结构再再挑战我们对于小说叙事的理解力,因此十分耐读,让人流连再三。
《年少友人》表面上说的是母亲年少时与几位亲密友人的故事,实则隐藏了一段难以启齿的秘密。女儿到了四十几岁还无法原谅母亲,即便已逝的母亲只能在梦中出现。故事一开场孟若写着:「…后来这梦再也没出现过,我想应该是因为这梦传达的想望太明显,宽恕又来得太轻易。」埋藏在女儿心里的魔障似乎永远也化不开。
郭强生老师说,这是一篇后设小说,故事中还有故事。而所谓的后设,在于叙事者思考的角度、理解事物的精神,而非写作的一种「形式」。于是乎,当中的弔诡就产生了,孟若跳脱一般说故事的手法而选择了难度较高的「后设」,代表故事中有无法直白诉说、隐而不显的黑暗面,必须透过小说家的精密设计,才能不流俗地写出一个平凡的故事。
以我目前的能力,孟若的短篇还是无法一眼望穿,有些故事读个两遍三遍、兜兜转转还不见得能厘清事件的真相(也许根本没有真相)。她像小津安二郎与Frank Gehry的混合体,打桩砌砖同时解构,看到正面也瞧见背面,可能阿桑到了60岁还在雾里看花,光就这点而言,读孟若的小说CP值太高。
Photo by Csilla Klenyánszki
https://www.riseart.com/art/bath-by-csilla-kleny-nszki
转载请注明源自 每日美剧 www.meirimeij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