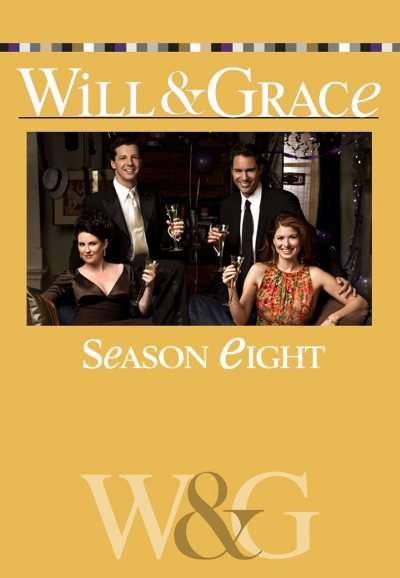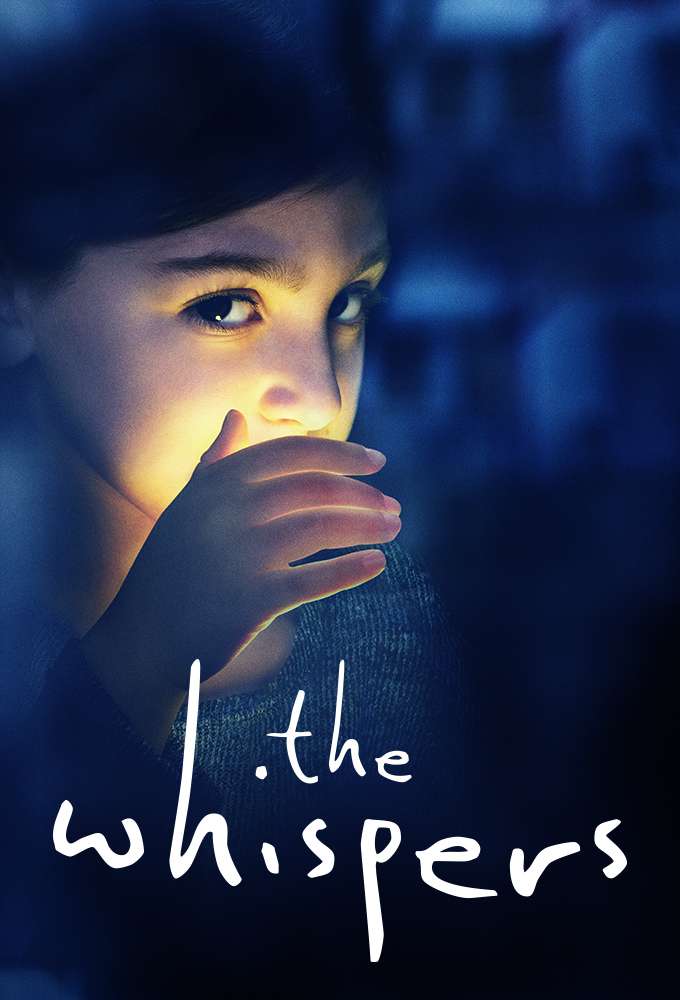我的美术史
最近看了九把刀新片,决定把九年前写的一篇散文贴出来。这篇文章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一段美术辛酸史。
我的手生来就会画画了。当然,如你所料,右手。
也或许,你并没有猜对。毕竟你没看过我画的图。
你有权亲眼看到图,再决定要不要猜下去。我有义务告诉你,大人们撞见我画出的第一张图,才恍然幼时我拿铁汤匙在碗里刮出刺耳噪音,是宣洩天份的有理取闹。彷彿我出生后三、四年,握起笔,又重生了一次。一只笔、一张纸,资质藏也藏不住。就算拿白布将我紧紧包复,打开后,照样送你一条美丽床单。
进幼稚园以前,大家即称我为小画家。我把姊姊的国语生字簿拿来画,蓝笔画满密密麻麻的铅笔字下方,完成一本图画故事书,惊奇如我画出弯曲的四肢,还有趴狗、运动选手,在大人眼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天赋,「章仔,以后不愁吃穿了,你儿子可以卖很多钱。」
爸,你的儿子以后可以卖钱。
他们小钱投资大梦,为我买下一叠叠计算纸,有时十三块一小本、有时十八块一大本,我画起连环图,往下翻,有连贯情节,看得大人们啧啧称奇,这出自一个幼童的天才之手。
一、网球赛
幼稚园第一堂绘画课进行五分钟,全班抬头愣看意气风发的我拿着作品走向老师,当老师展开画纸,同学们此起彼落的欣羨呼叹非但扬满这间教室,往后我上过课的每个班级也将承继这些,久之,我也就视之老天赋予的天资。然后,这些声音慢慢长大,溶进彩笔的颜色里,彷彿我的画笔能把它们的成长轨迹纪录下来。
国小一年级,我画图不必勾轮廓,照样涂得大家心花怒放,还记得第一回美术作业贴上后方黑板,围观同学顺着明君手指的方向望过来,「那张是他画的。」我知道她嘴里一定是这么说。还记得那张图只画了秋千、狗、几个人,但是对小孩子而言,也算宇宙全部了。第二次绘画课的题目「院子里」,我继而画了一个大圆圆、地球般的院子围墙,再把花花草草往院子里塞,至于衔接院子的房屋在哪里?没有人追究。明君每次去福利社买了五块一本的计算纸,就会分一半给我,条件要我每天画图给她看。多么简单而愉快的任务,当时我总认为以后会跟她结婚。小孩子怎会那么容易想要结婚?也许在他们的概念里,一个人独来独往是寂寞的,就像我画图,总希望旁有声音扮以讚美。
我喜欢讚美多过鼓励,虽然两者时而合一,但是我宁可把它们分开。因为后者,我不需要。我习惯讚美,有记忆以来,我画第一个图案就被讚美了。
国语课本教到爸爸的职业。花花绿绿的选项,我知道当老师讲到画家那一项,全班就会齐声嚷出我的名字,一切都在预期之内。我众望所归拿到整洁月绘画比赛第一名,因为没有第二个七岁孩童能够把人物比例画得跟真人不相上下,彷彿我脑袋里安装了一具齿轮放映机,喀哒喀哒把人形精确投映于画纸上。
所以画纸上人不会长翅膀,因为我们都没看过天使啊!
我是黄老师的骄傲,当我在社会课本节庆单元画出俊男美女结婚照,她等不及揣着本子飞奔到隔壁班炫燿:「怎么样?我们班有这样的学生!」;八开图画纸一张一块钱,来到我手中,竟纳入浩大的网球比赛,观众万头钻动,静晾后方自有其揽客活力,不只一次吸引路过的老师们闯进教室一探其恢弘壮阔。
每回礼拜二绘画课,我风风光光提着48色彩色笔走进教室,光芒夺目得教那些拥有60色彩色笔的同学羞愧得低下头。我得意。我的得意扩散至自然课心安理得收下同学帮我准备的方糖和冰糖,一点都不反省自己忘了带。
二、竹子
中年级导师姓谢,年约半百,对我的敌意出自春季旅行我一时走失害她紧张半天险些昏倒。从此小画家处处遭受刁难。寒假作业翻开读书心得,她会刻意挑我问:「你真的看过这本书吗?」
每班两名的绘画征件,她不选我,选了阿瑞,阿瑞甚至坦承了参赛作品是他妈妈代笔的。
日子这样进行到那天上午,班上走进一位转学生――小凯,成绩优异的他,一来便抢走谢老师的注意力,三番两次要把奖励往他身上塞,这也不奇怪,大夥有挑朋友的权利,当老师看腻了原有的班底,职业倦怠之馀,目光总会不由自主移向外来的未来主人翁身上。校园写生比赛那次,班上三个人被学校派去参加,有小凯,也有我。成绩公布,我拿下第一名,班上另个借我水彩笔的女生好心有好报得第三,唯独小凯落空。颁完奖,当天谢老师谈起这个让她五味杂陈的比赛,话也不客气了,挑明我走运,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谢老师性情诡怪,只是小学生视之当然,她琴弹得好,对美的鑑赏力也不低,但情绪控制每每让人不敢领教,升旗典礼只要早自习秩序不在优良之列,她抓狂之馀不揪出元凶决不罢休。
不过,起码每回美术课过后,她基于门面还是妥协的不让我作品缺席后方黑板。四年级教室后方黑板右边范围可贴八张图,一张张叠上,有次我画了八年抗战,日军持枪乱射栩栩如生,身历过那年代酸楚的谢老师看着图露出会心一笑,另一回我画了森林内吃人树攻击孤单小女孩,想像力充分发挥也没得挑剔。图纸只画一个人那次就没这么好运了,题目是「工作中的人」,我画一个灰姑娘般的女孩困身豪华客厅,谢老师逮着机会质问我:「你家具都画得很漂亮,但为什么只画一个人?」
「我想要表现一个人很辛苦的样子。」
「那你明明有画窗户,为什么窗户外面没有东西?」
「窗户太小,树画不下了。」
「你可以画竹子啊!竹子不是细细的吗?」
我哑口无言。有哪个小学生画植物主动想过要画竹子的?彩色笔粗粗一条笔直下来就是一根竹子了,几无修饰空间,要怎么画才能让人知道我画的是竹子呢?
谢老师的刁难我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但,画竹子,这念头像个解答无方的习题直刺我心底。当时风靡全台的电影正是〈鲁冰花〉,迷惘中我想,也许,我正如电影中那个以尺量画、徒具技术的乡长之子,画风华丽,却无从触摸艺术的核心,边都不到。毕竟我不是神童阿明。
我曾经是,在我误以为自己是的时候。
三、数学习作
画不出竹子的我,愣愣升上五、六年级。
成绩中等的我,第一次月考竟考了第一名,化为资优生阿瑞的眼中钉,一阵我考试作弊的谣言在班上扩散开来,我无端招来十一岁学童们口耳相传的冷嘲热讽,一句接一句。王老师就这样对我的印象定了调,每天上学水深火热,美术课的彩虹,看不到边际,亦触摸不着。王老师儿子读进阿瑞妈妈任教的幼稚园,交叉利益关系自此建立,同业互惠,皆大欢喜。
我常想,为什么本校没有专任美术老师,而是任由满眼偏见的导师身兼多职,他眼里既有的薄雾蒙蔽了辨识色彩的能力,常常我无能为力,只想躲进彩色笔盒里置笔凹陷处,教室这迷宫不够大,我凭自己的想像力朝下挖,渇望出口对我招手。
也因为如此,夜里,我在黑暗中以眼构图,有时画出一个大家为我庆生的蛋糕,有时画一个黑洞从老师身上烧开来。纸制品已在世界各处流通,没人阻止得了我发挥天赋。
我抓起彩笔打仗,拼命画、卖力画,我不知道终点在哪里,最后一张要画什么,但是,我朝迷惘的纸张用力涂厚。涂上红色,那是我受伤的色泽,也涂蓝色,那是我想要翱翔的天际,涂越多、纸就增重越不会随风飘起,逐渐,红与蓝颜料相渗,晕出我不想要的紫色,我搁下画笔,了解到,生活的进展,很多都不是我想要的,甚至那几张奖状也不是。电视剧播了「王昭君」,我乘兴把心中揣摩出来的古代美女们画上,很多时候,她们更像漫画。她们该是漫画吗?我知道,这样的时节,不会有正确答案送上门来,我只能掘土般朝纸面宣洩情绪,我的需索远远超过美术课所能给的,那些佔去一整个下午却只画一张图的课程、没带彩色笔就打手心的课程……
竹枝末端摇曳着狗尾巴草般的流苏,咻咻划过,那是老师手中挥洒不息的水彩笔。不必沾水,就能在空气中甩出萤光绿的视觉暂留。一瞬贯身的电亟,闪现我们对高年级身份的遵从和膜拜,我们咽下彩笔、画纸、橡皮擦所有,然后排队孤儿般盛取营养午餐,依序消化那些不得不吞的事物。
后来,我又拿到一张租税绘画比赛奖状,是第二名,得奖作品不具名贴上中廊,虽然我认为自己那张是最好的,但我庆幸学校增添不一样的审美观,不再无条件讚颂最精确的美丽。然而有天放学经过走廊,看到第一名同学坐在某班教室导师位子,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爸是学校的老师。
这张第二名奖状,使我取得参加校外写生比赛的资格,短短请了下午的假,返校后,发现有同学擅自从我抽屉拿出数学习作给老师批改,老师倒也大方落下红笔,由于还没写完,遂也不意外得到一堆二、三十分的难堪侮辱。这是我的同学。
这是我的学校,虽然建筑简单,班级不多,课程也依着教育部官方发布来走。但,有赖大白的真相,却是挖也挖不完,我想毕完业,许多谜团也将冰到最深处,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偷了鱼头的一百块,何以杨桃会当选模范生,也不再有人过问,这些多年后对大家人生历程来说不痛不痒的琐碎小事,默默冻进关节、膝盖,长大后我们还得模仿这些令人忽视的部位来折弯、曲解世上的一切。
画纸一摊,我试着画出学校平面图,凭借自己印象所及所去摸索,画出那些藏匿心中的不为人知。如果以后我是室内设计师,这张图等同预习,如果不是,那我就该画到更精细,把办公室人们的对话全都画出来,漫画般喷出烟雾,填入字句。我该画出我所想像的,他们眼中的我自己。
我,自己,踽踽走完一巡美术坎坷史。
在重新抵达自己生肖的那一年,我即将毕业。
不免俗,学着别人买起毕业纪念册。空空白白的新册子,拿着第一个就给一年级导师签,要她替我保留美好的开始。剩下的,都不必放心上了。
那些老师光看画纸,就能识别你用几色彩笔的时光──我可以活用水彩,来回避这样的探测。我也可以叛逆的不加水使用水彩,以拖曳出大人们难以理解的干涸印迹,在图纸上。然后强解那是他们所无法领会的艺术境界。
水彩的姿色可以永远保留,但颜料的香味却闻一遍就没了。
当画画的乐趣在收笔的一刹那间告一段落,赏画人的品头论足尾随而至,我不予理会。
谢老师逼问我的画竹难题,我至今没有解答,却偶然旋绕脑际,那些藏匿于我关节、膝盖里的灾情,都学起了竹子,翩然摇曳。不论我的美术史会如何走向总结,我起码穿梭了他人这个阴暗的人格夹层,提炼出更多创作的灵感,一切变得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也由于这段旅程,使我右手不仅画图,也写下满心悸动,左手则贴上心田,覆盖遍野的感激。
因为感激,所以当我回过来看,他们也不再是以前的阿瑞、谢老师,不再是小凯了。
他们是磨厉、激发我的人。他们烹调出我生活中酸涩的小小切片,拼贴成我美术历程里罕见的竹子,节节叠高,高至我撞上一片竹叶,扬头思忖竹叶带来的节庆。
一片新绿,远超出颜料所能描摹、所能企及。
转载请注明源自 每日美剧 www.meirimeij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