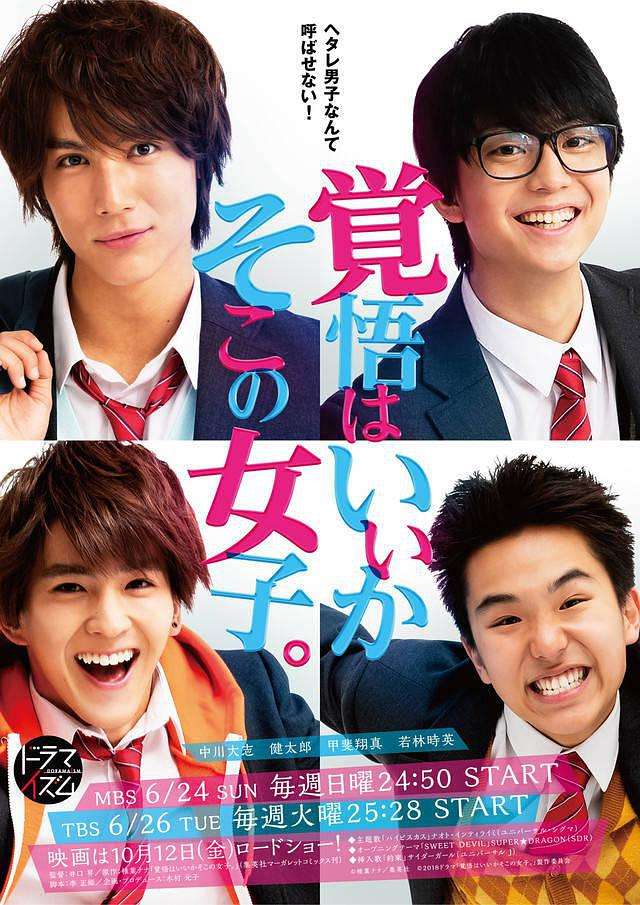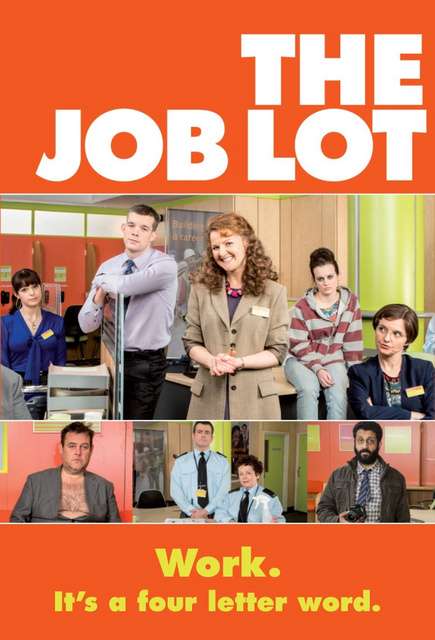王明台【顺云/Cloudy】(2017)
蔡 玮 发布于 2017-11-04
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关系吧。因为家人原不该相互伤害,伤人的话本可以不听、不信
撰文/蔡玮
顺云回想母亲对自己的好,是否因为只有自己是陪在身旁唯一的子女,不得而知。如今,生命里失去的已经无法挽回。顺云对已婚主任多年来的情愫,想必母亲是知情的,但从未阻止,更别说交心。否则,顺云可能在心理上会感觉好过些。至于闯空门的事,母亲完全不知情,也怪不得她。关于人生中的苦难,她早已习惯一个人承受,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已经是如此。这个家就是这样,如果这还能算是个家的话。
不变的湿冷的冬天。面对港口的老旧公寓彷彿是要与活着的人竞赛,坚持到岁月的尽头。顺云站在公寓天台的高处,她拿不定主意是要弃权认输,还是坚持下去。她感觉人生的筹码已经用尽。或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被人刻意的剥夺掉。
与顺云同样处境做为家庭留守者的,还有隔壁的小女孩。如果此刻顺云知道她小小年纪所面对的,她或许会燃起生命的馀温,替同是受害者挺身而出。毕竟,顺云最大的不幸,是她始终以为是她一个人独自承受了所有的苦难。
顺云的遭遇,让我联想起许多四年级、五年级的朋友的遭遇。一个人的专注力其实有限,顶多不超过一到一个半声音的频宽。因此,对身边的人日夜不停的叨絮、抱怨,会是怎样的一种残酷,甚至剥夺了听话人内在真正的声音。顺云真的没有发展出一点让自己喜乐的嗜好?好让没有母亲的日子可以享受一个人自己发光发热的喜悦?我希望她是有的,又或许她还有机会去找寻,如果她想到的话。
在最后的生命里,顺云的母亲甚至退化成一名任性的少女的心态。而她同时又是顺云在家中唯一的尊长。是不是因为后者,造成她毫无顾忌、任意中伤自己女儿的任性行径?为何母亲又要不断地重复她所坚持的、家庭关系的历史版本,且不顾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抗议,毫不考虑变换一种态度、或做些修正—让家中的气氛更融洽些,这样对她本人又有什么好处?
我以为,家庭做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主要受一套意识型态的治理。意识形态反应人对环境的认知,发展成一套主观模式,内容决定了家庭资本与劳力投入及产出的分派,从而减省了交换的成本—衡量、实施、守法(规则的合法化与执行)等都有正质的成本。一个大家族中地位最尊的大家长,有时会假装成没声音的人,因为年节的仪式就充分表彰了他个人在家庭组织中的地位。她或他只要行礼如仪,就可以主持一套家庭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如儒家的家庭伦理教条。这让我联想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几乎家家都有个坚持周末全家人一起同桌吃饭的父亲。
至于家中的母亲角色,则因为不堪长年替家人准备餐桌上食物等沈重家务的负担,几乎感受不到仪式的心理加持,更不用说实质的补偿或劳务的分担。她往往会将多年的抱怨,混杂产生出一套主观的家人关系历史的论述,这是她简化主导家庭资源、劳务交换之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容—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决定正义的特质(Douglass Cecil North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1981)。往往这里面没有子女的地位,尤其没有未婚或未能增加家庭收益的成员的地位。而,不变的是对父母有所亏欠的子女,为子女牺牲受难的母亲,甚至从小就显露「不良品性」的成员,暗示后者从一开始就不应具备任何的发言权。这样的论述佔据了家人团聚的时光,变得徒具形式令人厌恶,更别说彼此之间感情交流、生活事务上的交换心得。
这是为何顺云被母亲一套的论述,剥夺了对所承担的家庭劳务的发言权,甚至接受家人拥抱感受情感支持的权力。除非外力的介入或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如家人出外工作带来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的提昇,否则母亲是不可能也不会主动修正、更别说放弃她的那一套爱恨交织的家庭历史故事。
母亲终于从受害者转变成加害人,作为子女的即使知道真相也难以启齿。家庭论述的语言暴力,最伤害的是对家人感情的分化。被数落的感到孤立,没被数落的置身事外。久而久之就不相往来,兄弟姊妹比朋友相知更少。当事人该如何自处?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关系吧。因为家人原不该相互伤害,伤人的话本可以不听、不信。接着再思考日常生活中力有所及之处,往上增加家人的待遇—只要是人都会做出的回馈、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且做了就不论毁誉。这庶几不会造成遗憾吧。这或许能让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顺云自救。(蔡玮,20171031顺云)
导演:
王明台 Ming-Tai Wang
编剧:
王明台 Ming-Tai Wang
温郁芳
演员:
陈季霞 Chi-hsia Chen ............韩顺云
刘引商 Yin-Shang Liu ............韩李氏(顺云母)
柯一正 ............杨秉宏主任
(atmovies.com)
撰文/蔡玮
顺云回想母亲对自己的好,是否因为只有自己是陪在身旁唯一的子女,不得而知。如今,生命里失去的已经无法挽回。顺云对已婚主任多年来的情愫,想必母亲是知情的,但从未阻止,更别说交心。否则,顺云可能在心理上会感觉好过些。至于闯空门的事,母亲完全不知情,也怪不得她。关于人生中的苦难,她早已习惯一个人承受,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已经是如此。这个家就是这样,如果这还能算是个家的话。
不变的湿冷的冬天。面对港口的老旧公寓彷彿是要与活着的人竞赛,坚持到岁月的尽头。顺云站在公寓天台的高处,她拿不定主意是要弃权认输,还是坚持下去。她感觉人生的筹码已经用尽。或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被人刻意的剥夺掉。
与顺云同样处境做为家庭留守者的,还有隔壁的小女孩。如果此刻顺云知道她小小年纪所面对的,她或许会燃起生命的馀温,替同是受害者挺身而出。毕竟,顺云最大的不幸,是她始终以为是她一个人独自承受了所有的苦难。
顺云的遭遇,让我联想起许多四年级、五年级的朋友的遭遇。一个人的专注力其实有限,顶多不超过一到一个半声音的频宽。因此,对身边的人日夜不停的叨絮、抱怨,会是怎样的一种残酷,甚至剥夺了听话人内在真正的声音。顺云真的没有发展出一点让自己喜乐的嗜好?好让没有母亲的日子可以享受一个人自己发光发热的喜悦?我希望她是有的,又或许她还有机会去找寻,如果她想到的话。
在最后的生命里,顺云的母亲甚至退化成一名任性的少女的心态。而她同时又是顺云在家中唯一的尊长。是不是因为后者,造成她毫无顾忌、任意中伤自己女儿的任性行径?为何母亲又要不断地重复她所坚持的、家庭关系的历史版本,且不顾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抗议,毫不考虑变换一种态度、或做些修正—让家中的气氛更融洽些,这样对她本人又有什么好处?
我以为,家庭做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主要受一套意识型态的治理。意识形态反应人对环境的认知,发展成一套主观模式,内容决定了家庭资本与劳力投入及产出的分派,从而减省了交换的成本—衡量、实施、守法(规则的合法化与执行)等都有正质的成本。一个大家族中地位最尊的大家长,有时会假装成没声音的人,因为年节的仪式就充分表彰了他个人在家庭组织中的地位。她或他只要行礼如仪,就可以主持一套家庭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如儒家的家庭伦理教条。这让我联想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几乎家家都有个坚持周末全家人一起同桌吃饭的父亲。
至于家中的母亲角色,则因为不堪长年替家人准备餐桌上食物等沈重家务的负担,几乎感受不到仪式的心理加持,更不用说实质的补偿或劳务的分担。她往往会将多年的抱怨,混杂产生出一套主观的家人关系历史的论述,这是她简化主导家庭资源、劳务交换之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容—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决定正义的特质(Douglass Cecil North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1981)。往往这里面没有子女的地位,尤其没有未婚或未能增加家庭收益的成员的地位。而,不变的是对父母有所亏欠的子女,为子女牺牲受难的母亲,甚至从小就显露「不良品性」的成员,暗示后者从一开始就不应具备任何的发言权。这样的论述佔据了家人团聚的时光,变得徒具形式令人厌恶,更别说彼此之间感情交流、生活事务上的交换心得。
这是为何顺云被母亲一套的论述,剥夺了对所承担的家庭劳务的发言权,甚至接受家人拥抱感受情感支持的权力。除非外力的介入或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如家人出外工作带来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的提昇,否则母亲是不可能也不会主动修正、更别说放弃她的那一套爱恨交织的家庭历史故事。
母亲终于从受害者转变成加害人,作为子女的即使知道真相也难以启齿。家庭论述的语言暴力,最伤害的是对家人感情的分化。被数落的感到孤立,没被数落的置身事外。久而久之就不相往来,兄弟姊妹比朋友相知更少。当事人该如何自处?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关系吧。因为家人原不该相互伤害,伤人的话本可以不听、不信。接着再思考日常生活中力有所及之处,往上增加家人的待遇—只要是人都会做出的回馈、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且做了就不论毁誉。这庶几不会造成遗憾吧。这或许能让社会上许许多多的顺云自救。(蔡玮,20171031顺云)
导演:
王明台 Ming-Tai Wang
编剧:
王明台 Ming-Tai Wang
温郁芳
演员:
陈季霞 Chi-hsia Chen ............韩顺云
刘引商 Yin-Shang Liu ............韩李氏(顺云母)
柯一正 ............杨秉宏主任
(atmovies.com)
转载请注明源自 每日美剧 www.meirimeij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