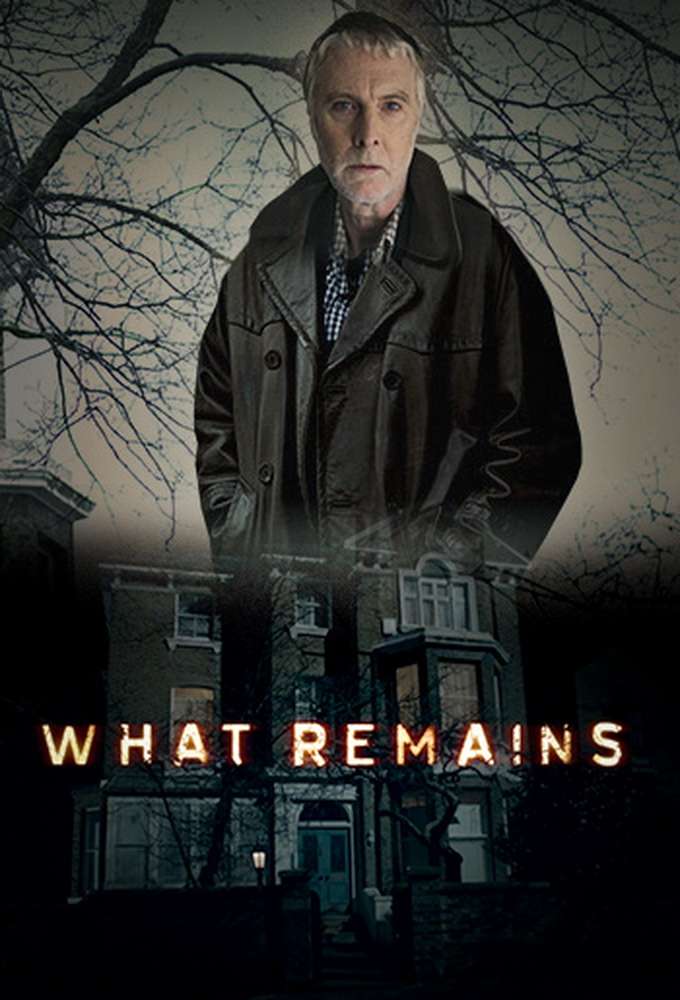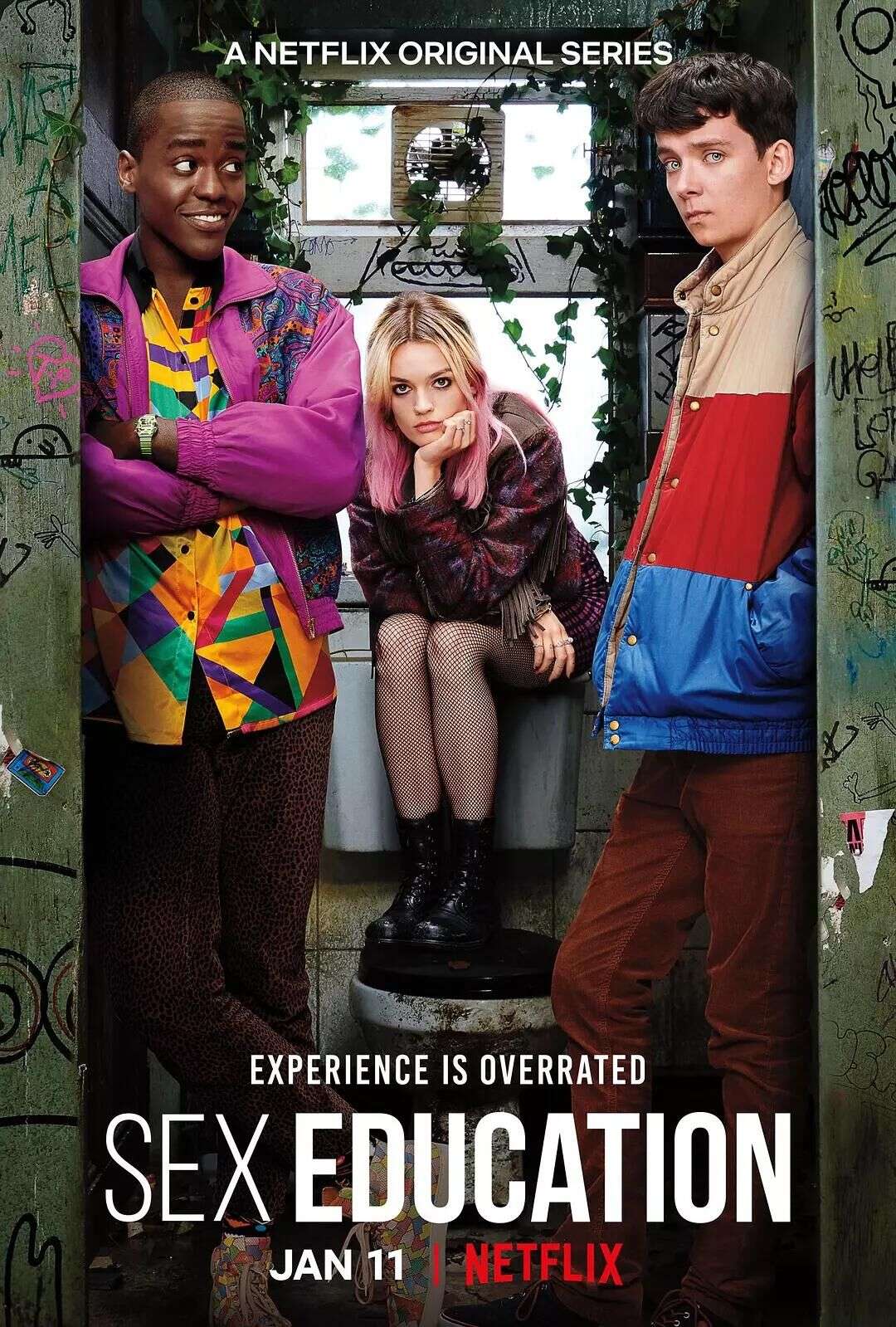林明谦【看不见的台湾/A Journey with Invisible Friends】(2018)
蔡 玮 发布于 2018-05-26
一个没有语言暴力、死亡威胁的不朽的世界
撰文/蔡玮
宝贵与阿姐这一对灵媒与翻译组合,让我想到生成语法与一般语言的关系。生成语法是未组织为一般语言前的状态,据学者说那是人类先天具有的、普同的语言能力。这又让我对本片的语言的世界,产生丰富的想像。
布赫迪厄认同巫术仪式的实践者,灵感的来源与一般艺术家无异,只是实作的场域与工具有别。
我以为,萨满、巫师的灵感无非是以生成语法的构成首先成型,而灵媒则特别将这因此产生的语言寄讬在一个指称的目标—比如妈祖、延平郡王、或玉皇大帝的儿子,透过翻译再组织成一般人能理解的语言。我认为本片中的「天语」翻译者阿姐,她独特的绵长句子、驰骋的修辞空间,俨然是一位文学家、雄辩术专家。
社会学家布赫迪厄认为,巫师的仪式行为,与一般传统社会的实作经济学的操作性质相同。人因所处的社会自然产生的习性,让社会的组织复制、再生。我以为习性中至为关键的莫过于语言。
传统社会的实作经济实践者,在各自的场域,累积各种价值资本、在交织重叠的网路间彼此交换、交易,求整体利益的累积、增值。在本片中,我看到由灵媒代言的神明,所祈求的无非也是个人或族群的兴旺,如延平王求「昇云」远离在世前间的的爱恨纠葛、导演因灵媒的引导具备了透过超渡九二一地震的亡灵替祖先累积功德、除晦同时庇荫子孙的动机。我又看到古老的社会中的价值观,透过一连串神明主导、灵媒与翻译代言的实作,一步步的复制重生,甚至规模与意义超过以往—我是想到在片中延平王邀请西拉雅的祖灵阿立祖,在各自的灵媒、女巫师的引导、道教法师的主持仪式下,一同经历在鹿耳门举行的超度法会的浩大场面。
就在那个独特的时空底下,神明的和解象征性的为人间有情的福祉种下了福果。这是如何达成的?在阿姐与宝贵的心中,预先有了这样的大和解图像,再与纪录片的剧组协调、编排促成?我宁愿相信每次的降灵事件,灵媒与翻译只能掌握「天语」的有限的方向,透过后者的在场主述一边「剧透」一边下达任务指令一边扮演神明的话语一步步推演而得,事先并未能预见其结果。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语言犹如游戏,游戏的参与者掌握语言使用的同时也掌握了规则以进一步行动,—比如下棋。语词就如同棋子—同时暗示了角色与规则,或路标—引导前进但每次只是一个笼统的方向。正因为语词像多脚椅—每个脚都是一则描述给予的(语意)支撑,毁了一脚(一个使用注释失效)却依旧是椅子能够挺立。它不如数学符号边界清晰、定义完整,却因为这样的笼统缺陷,能够让游戏不断地朝任何可能的方向进行、翻新玩法(维根斯坦,哲学研究)。而一个新的玩的方式就代表一个新的意义的诞生。在这样的世界里,我看到了一个永恒的世界,语言是主体,人只是能掌握语言使用潜能的自动机械—对指称目标产生的内心图像做出反应又因此成为随机图像参数的函数,但语言又因为人自动创造新的指称符号得以不断地进行(语词)亲族间的交叠、繁衍、扩大。维根斯坦就曾在书中提到,世界是由简单事实组成。简单事实则由简单对象组成。简单事实不可再分割,而各自独立(罗素,逻辑原子论)。在本片中,我看到「和解」这个简单的事实座落在永恒世界的中心。
观赏者如果能「理解」本片的「意义」,就一定能体会到片中所暗示的形而上的美学,与伦理的诉求。不过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如何能让语言自动的「生成」,而不妨碍它的生态。我在片中见到了一个没有语言暴力、死亡威胁的语境。我同样在片中见识到「意义」并非等于能指的目标的实作。否则,没有实体存在的神明如何能透过代言者与翻译的言语在人间有所作为—因为语言指称的功能超越了物理的限制与界线?这样的世界—一个由无实体的主体所推动的语言与象征的剧场,一个能满足所有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公同共好的嗜欲的成就,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这是现实的物理世界之外、由人类的语言潜能打造的「可能」的世界,也是我们这个反对文字狱、思想压制的社会所能享受的独特的资产、与赋予。人一开口,果真世界就存在着无穷的可能性。(蔡玮,20180526看不见的台湾)
撰文/蔡玮
宝贵与阿姐这一对灵媒与翻译组合,让我想到生成语法与一般语言的关系。生成语法是未组织为一般语言前的状态,据学者说那是人类先天具有的、普同的语言能力。这又让我对本片的语言的世界,产生丰富的想像。
布赫迪厄认同巫术仪式的实践者,灵感的来源与一般艺术家无异,只是实作的场域与工具有别。
我以为,萨满、巫师的灵感无非是以生成语法的构成首先成型,而灵媒则特别将这因此产生的语言寄讬在一个指称的目标—比如妈祖、延平郡王、或玉皇大帝的儿子,透过翻译再组织成一般人能理解的语言。我认为本片中的「天语」翻译者阿姐,她独特的绵长句子、驰骋的修辞空间,俨然是一位文学家、雄辩术专家。
社会学家布赫迪厄认为,巫师的仪式行为,与一般传统社会的实作经济学的操作性质相同。人因所处的社会自然产生的习性,让社会的组织复制、再生。我以为习性中至为关键的莫过于语言。
传统社会的实作经济实践者,在各自的场域,累积各种价值资本、在交织重叠的网路间彼此交换、交易,求整体利益的累积、增值。在本片中,我看到由灵媒代言的神明,所祈求的无非也是个人或族群的兴旺,如延平王求「昇云」远离在世前间的的爱恨纠葛、导演因灵媒的引导具备了透过超渡九二一地震的亡灵替祖先累积功德、除晦同时庇荫子孙的动机。我又看到古老的社会中的价值观,透过一连串神明主导、灵媒与翻译代言的实作,一步步的复制重生,甚至规模与意义超过以往—我是想到在片中延平王邀请西拉雅的祖灵阿立祖,在各自的灵媒、女巫师的引导、道教法师的主持仪式下,一同经历在鹿耳门举行的超度法会的浩大场面。
就在那个独特的时空底下,神明的和解象征性的为人间有情的福祉种下了福果。这是如何达成的?在阿姐与宝贵的心中,预先有了这样的大和解图像,再与纪录片的剧组协调、编排促成?我宁愿相信每次的降灵事件,灵媒与翻译只能掌握「天语」的有限的方向,透过后者的在场主述一边「剧透」一边下达任务指令一边扮演神明的话语一步步推演而得,事先并未能预见其结果。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语言犹如游戏,游戏的参与者掌握语言使用的同时也掌握了规则以进一步行动,—比如下棋。语词就如同棋子—同时暗示了角色与规则,或路标—引导前进但每次只是一个笼统的方向。正因为语词像多脚椅—每个脚都是一则描述给予的(语意)支撑,毁了一脚(一个使用注释失效)却依旧是椅子能够挺立。它不如数学符号边界清晰、定义完整,却因为这样的笼统缺陷,能够让游戏不断地朝任何可能的方向进行、翻新玩法(维根斯坦,哲学研究)。而一个新的玩的方式就代表一个新的意义的诞生。在这样的世界里,我看到了一个永恒的世界,语言是主体,人只是能掌握语言使用潜能的自动机械—对指称目标产生的内心图像做出反应又因此成为随机图像参数的函数,但语言又因为人自动创造新的指称符号得以不断地进行(语词)亲族间的交叠、繁衍、扩大。维根斯坦就曾在书中提到,世界是由简单事实组成。简单事实则由简单对象组成。简单事实不可再分割,而各自独立(罗素,逻辑原子论)。在本片中,我看到「和解」这个简单的事实座落在永恒世界的中心。
观赏者如果能「理解」本片的「意义」,就一定能体会到片中所暗示的形而上的美学,与伦理的诉求。不过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如何能让语言自动的「生成」,而不妨碍它的生态。我在片中见到了一个没有语言暴力、死亡威胁的语境。我同样在片中见识到「意义」并非等于能指的目标的实作。否则,没有实体存在的神明如何能透过代言者与翻译的言语在人间有所作为—因为语言指称的功能超越了物理的限制与界线?这样的世界—一个由无实体的主体所推动的语言与象征的剧场,一个能满足所有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公同共好的嗜欲的成就,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这是现实的物理世界之外、由人类的语言潜能打造的「可能」的世界,也是我们这个反对文字狱、思想压制的社会所能享受的独特的资产、与赋予。人一开口,果真世界就存在着无穷的可能性。(蔡玮,20180526看不见的台湾)
转载请注明源自 每日美剧 www.meirimeij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