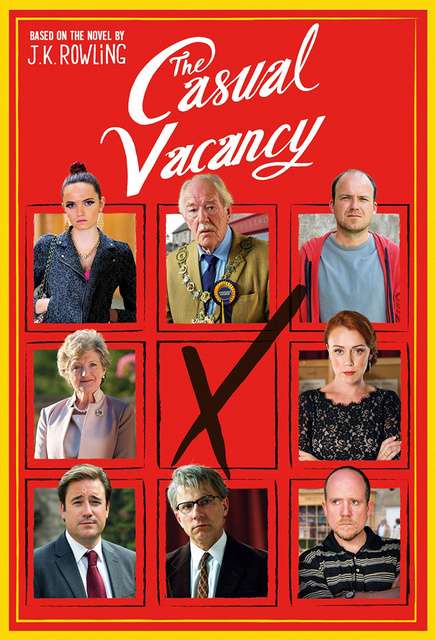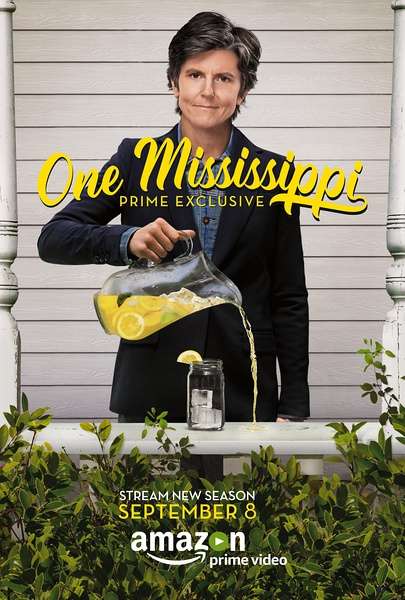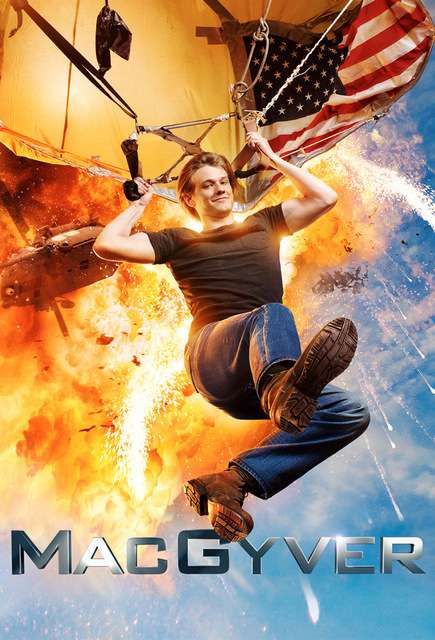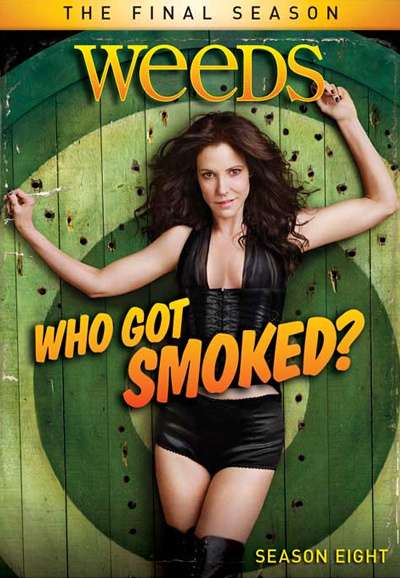印尼艾可舞团双舞作-溯源、寻根,是创作者必须走的不归路。

听着印尼艾可舞团编舞家苏布利阳托说着他自己及舞团的故事时,脑中突然浮现布拉瑞扬的面孔,就觉得,这两个艺术家好像啊!
他们都曾在国际舞台上辉煌过,却也在绚丽的际遇中迷失了自己,他们最终都决定返乡溯源寻根,而现在,他们都开了一条偏乡小孩过去从没想过、或根本不敢想的舞蹈路。
两人之间的很多巧合点都很有趣。
首先,在辉煌时期,两人都受惠于美国舞蹈艺术节(ADF),布拉瑞扬曾两度受邀参加,苏布利阳托也在1996年参与;两人都在美国待了一段日子,布拉瑞扬2011年在纽约林肯中心的演出大获好评,苏布利阳托则入选美国流行音乐巨星玛丹娜国际巡演的6人专属舞团,后来并在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担任舞蹈顾问,感觉两人都有大好前程等在前头。
两人的自我怀疑也都在人生的高峰时产生。

在林肯中心的舞牵着玛莎葛兰姆手谢幕时,布拉瑞扬想到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牵着自己舞团孩子的手,在舞台上一起谢幕,该有多好?」这个想法在回台湾后慢慢酝酿成返乡寻根的念头。
苏布利阳托则是在二度赴美 ,花了3年拿下硕士学位后,突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是谁?」
「我是个好舞者吗?」
对于自己追求的舞蹈这条路,好像接近了目标,却又不是那么确定,最终他决定要回印尼寻找自己。
更巧的是,布拉瑞扬2014年回台东成立了舞团,苏布利阳托也在同一年回印尼,并收到来自偏乡贾伊洛洛的官方邀请,请他带着当地贫困的街童进行舞蹈创作。
台东原本没有现代舞团,所以有舞蹈梦的孩子,只能往台北跑,布拉瑞扬在成立舞团前在台东做的作品《勇者》,叙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有人为了上舞蹈课半工半读,有的因爸妈反对只身离家,专业舞者,在东部的饭店为观光客跳舞,布拉瑞扬舞团的成立,让这些在地的舞魂有了归宿,成立以来,年年都有新作品推出。
苏布利阳托也在贾伊洛洛进行无中生有的行动,他先花了两年研究当地的文化传统,他发现当地年轻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根本不重视 ,袋里想的出路就是当军人、警察、护士或公务员。
但跟这些孩子一起生活的经验,让他体会到贾伊洛洛的美好。
「他们强迫我要潜水。」苏布利阳托说:「我一再拒绝,他们一再邀约,很坚持。」最终他无奈听从众潜入水中,却大开眼界,「鱼、珊瑚礁很美,人为的破坏很丑。」
这次带来台湾的双舞作之一的《哭泣贾伊洛洛》探讨的就是这样的议题,舞作中7名男舞者身穿红色短裤模仿鱼群,提醒人们贾伊洛洛正受到过度开发的威胁,期待海洋生态癒合,珊瑚礁不再崩解,鱼群再次回归,水之神灵复元。

双舞作的另一个作品《Balabala》则为东印尼偏乡女性发声,「在这个地区女性地位很低。」苏布利阳托说:「丈夫鞭打老婆很常见,女性被压迫得很厉害。」
在这个地区,女性的功能就下厨做菜,上床做爱,伺候丈夫,照顾小孩,这是个渔乡,丈夫负责抓鱼,把鱼搬下船的却是老婆,把鱼烧成菜的也是老婆。
「我妈妈在家里也是这样的地位。」苏布利阳托说:「她在我随玛丹娜巡演时过世,所以,这个作品的发想也是源自母亲的故事。」
《Balabala》是把印尼的战舞解构编成,在印尼,战舞是专属于男舞者的舞,如果找女舞者跳,会引起议论,甚至会被严重警告,但苏布利阳托把它解耩了,全由女舞者跳,把杀气十足的阳刚气转化为具有女性特质,既柔又美的英气,这样的解构巧妙地化解了可能会有的阻力。
有趣的是,布拉瑞扬回原乡后,走的也是解构重组的路子,有人问他返乡否要创作属于原住民的舞蹈,他说不是,「我就是从生活中学习,把在台东生过中体会到的感觉舞出来。」它可能有点原住民味道,但却也不尽然是。
这么像的两个人,或许应该找一天见个面,摆几瓶小米酒,来场痛快的秉烛夜谈。
(图片由两厅院及印尼艾可舞团提供)
印尼艾可舞团《哭泣贾依洛洛》、《Balabala》双舞作演出资讯
演出时间
7月14日 19:30
7月15日 14:30、19:30
7月16日 14:30
演出地点:实验剧场
转载请注明源自 每日美剧 www.meirimeij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