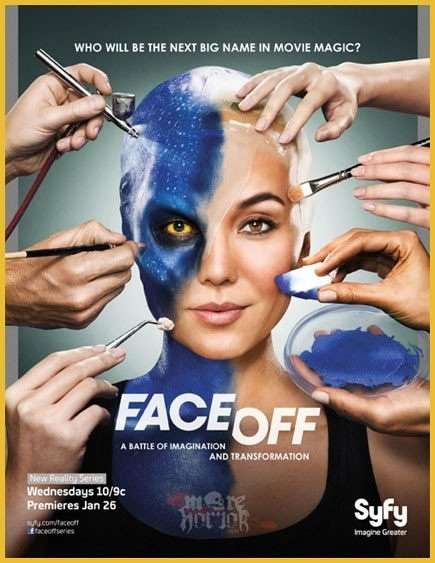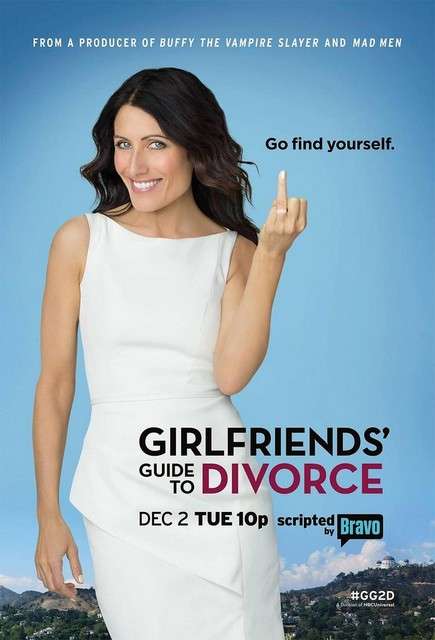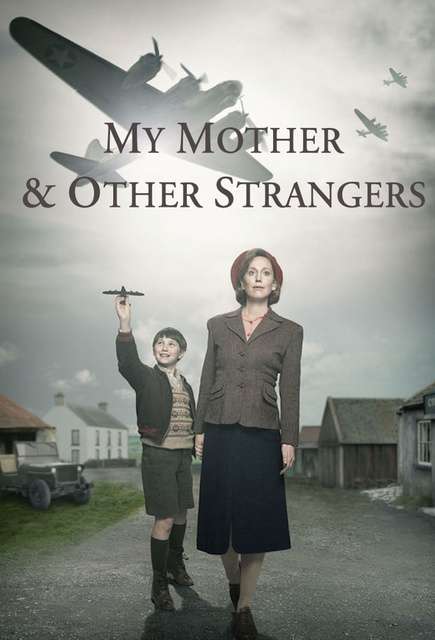一首在戏剧舞台上的Rondo – 香港话剧团「父亲」

简单说,「父亲」是一出讲「认知障碍」的戏,剧作家非常有趣地从病人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虽然,观众可能到第二或第三场戏才会发现这件事。也就是因为选择了这个角度,所以整出戏,就变成了一首真真假假,无限循环的Rondo。(开启Rondo恶梦模式)
这是继「最后晚餐」,我第二次看冯蔚衡导演的戏,两部戏的共通点是,冯导似乎偏爱,用「悲伤的故事」来传达「正面的能量」。坦白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辛苦的选择,毕竟,用「开心的故事」叙述「人生的悲哀」,观众要投入会容易许多。
整体而言,我还算喜欢冯导处理戏剧的节奏,干净、清楚而简单。「父亲」是一首非常混乱的Rondo,不论是演员或者观众,都非常容易在那些看似相同,却又不同的无限循环中迷失。但导演非常巧妙地让这些复杂而混乱的线条,最终用着非常干净而简单的方式呈现。作为观众,你不需要去分析剧作家是怎样架构文本,不需要分神去思考每一幕中间的连贯,也不需要去猜想现在这一幕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每一段故事,就这样自然地呈现在眼前,能够在这么舒服的状态之下,享受一出这么复杂的演出,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啊!(当然,演员们也功不可没。)
不过,基于本人是个比较接近暗黑版Pierre的节奏控观众,不论是「最后晚餐」或是「父亲」,对我来说速度感都略显温吞,有点难让人进入真正的感动。导演或许是刻意淡化整出戏的情绪起伏,但就故事铺排来说,在没有太明显速度及音量变化之下,张力却显得不足。Andre突然觉得女儿想要谋夺家产,Anne一边在父亲和男友中间拉距,又一边要接受父亲永远只记挂妹妹的冲击,导演的处理,都让这个法国剧本,「用着香港人的角度,活在传统的华人世界里」。
整出戏,除了毛Sir的Andre几次讲出「伦敦那个地方,一年到头都下雨啊!」可以让人看到法国人对于英国的嘲弄之外,大概就只剩高翰文的Pierre不停在提醒观众,他们是法国人了吧!喔!还有,就是幸好剧本,还记得让Anne说了「佢唔系一条友,佢系我锺意既男人。」(法国人万岁!)

坦白说,如果不是我实在坐得很近,还真的有看到Anne眼中的泪水在那里转了一下,我真的有一种,想要对着他们说,「C’est la vie! Just stay or go!」的冲动。(显示为观众开始走神,急需快转。需知道爸爸不会等你决定好了才老,当老人家即使退化却还这么可爱这么优雅这么俏皮的时候,请感恩惜福。)
不过,本人自己暗黑,剧场也还是需要一些温暖的导演啦!(我还是非常期待有一天,冯导能用这样的精神,导出让我这种暗黑版观众都会忍不住感动的一出戏!)
节奏上的温吞以及张力不足,直接影响到了毛sir的角色。没看过毛sir演戏,自然也不存在着任何预设立场。坦白说,能够一出场不讲话,光是站在那边就抓住观众全部注意力,全身是戏的神级演员,真的不多,不论台港。更不要说,当一个演员拥有历练时,也意味着他同时面对着体力和记忆力的考验,如何努力延长自己生理和心理的巅峰时刻,真的是每一个好演员一辈子都不能放下的功课。
毛sir的演出算是中规中矩,没有太多洒狗血的大起大落,但你还是能看到一个优雅的绅士,一步一步走向退化,最终返璞归真的那个过程。10/20那场,些许感觉Andre和其他演员之间流动的线条并不是太顺,整体感觉比较像是看毛sir个人秀,(但如果以个人秀的标准来看,这戏就真的也太平淡了。)然而这个情形到10/21那场已经完全消失,演员彼此间交棒显得顺畅许多。

Andre唯一让我比较失望的是,从跳踢踏舞,到最后如同孩子般找妈妈的过程,你并没有看到「一个崩塌的老人」。因为这个老人,他在跳踢踏舞的时候已经显得老态,但当他忘记自己是个老人时,却也没办法从他的肢体动作中,看到那种身心不协调的挣扎。当你要说服观众,这个老人,确实已经对Anne和Pierre的生活造成困扰,确实有不得不被送去疗养院的必要,也得要有确实对应的表现才行啊!就剧本而言,或许以法国人的角度,这样的理由已经足够了,但还是那句,导演并没有真的让我感受到,他们是法国人啊!
(虽然我承认我私心比较希望看到一出,超级洒狗血可以在剧场哭到昏倒的大悲剧,但我真的觉得Andre不够明显的性格和动作落差,已经不是导演试图淡化悲剧所可以解释的了。)
以下的部分,大概会是我写过,最不白话的一段心得,但却是我觉得最贴切地形容,所以,我决定还是保留。
先不讨论Anne和Pierre两个角色的诠释,先来说说,当我坐在台下,看着这两位演员的演出时,脑中闪过的想法。

如同我一开始所说,这部戏对我而言,是一首难缠的Rondo,而台上不算多的演员,就像是一组木管五重奏。对我而言,一组木管五重奏,我可以接受Clarinet吹错音,可以接受Flute音准不自主一直偏高,但我完全不能忍受,每换一段就下错速度的Oboe,或是老是打不稳拍子的Bassoon。
对一般听众来说,或许永远只注意到吹着花俏旋律的Clarinet和Flute,却不了解,可能只是偶尔吹个几句主题的Oboe,和可能从头到尾都没被听众注意到的Bassoon,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重要。前面的状况,就像是偶尔遇到演员吃螺丝,最多就是,嗯,错了,但音乐通常还是可以继续流畅地走下去,但遇到后面的状况,曲子随时可能变成一场闹剧,到那时候,听众应该只想跳上台,请他们立刻停止演出吧!
而同样地,当你发现一支好的Oboe,或是一支好的Bassoon时,那种兴奋也是立即而真实的。对我而言,彭杏英的Anne,就是那支在混乱剧情铺排之下,永远为下一段演出,准确下速度的Oboe,而高翰文的Pierre,就是那支,不管曲子现在是交错拍、变态拍,还是混合拍,都用着稳定速度吹出和旋低音的那支Bassoon。
印象很深,10/21那场,某一幕,我真的在那一煞那,突然有一种,遇到一支拍子超稳的Bassoon,非常开心知道自己可以直接翘脚不用数拍子(大误)的兴奋感啊!(忘记是哪一幕了,大约就是,Pierre某次拉开西装外套手叉腰,然后忘记缩小腹的那幕吧!)

至于阿Anne,是10/20那场,我因为前一晚真的没怎么睡,有点晃神之下,支撑我看完整部戏的主力。很稳,很定,让人很放心的角色演出。(这好像不是称讚?!不要闹!这真的是称讚!至今被本人列为此类压台等级的演员,应该不超过十个!)(不过这样讲好像不太公平,毕竟,不是每个角色站上台都是为了压台而存在,只是Anne刚好是这样的角色啦!)
喜欢Anne的部分包括了,Anne每一次说出,「我地要倾下」(确切的字眼我忘记了)时,帮每一幕开场所下的注脚。喜欢Anne说出「那是我锺意既男人」以及「我系真系锺意佢」时,那种安静的笃定,(感谢导演跟演员没有在这个部分洒狗血)。喜欢Anne最后对着观众席说对白的态度(但我完全想不起来那段在说什么了)。
基于,太过放心看得太舒服,所以真的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挑一下,我觉得稍有落差的部分说一下好了。(我果然是个critical的观众,阿Anne我对不起你,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啦!)

Anne背对着观众,说出掐死父亲的梦境那场戏,10/20坐的位置只能看到背影,看不到出场前以及手部的动作,说真的,声音表情100分。但10/21那场,换了一个方向的座位,看到全部的演出时,我反而有一种,Anne并没有确实表达出,一个照顾者在面对这种场景时,同时存在着那种因为受过教育而产生的自厌,纯动物性的生存本能,面对未知的惶恐,以及有口说不出的痛苦。
我不知道是因为导演的安排还是什么,但我真的觉得这段的Anne从一出场的转身开始,就太优雅了!愈是well-educated,愈是「孝顺」的人,在面对这样的自己时,应该是愈不能接受,反弹愈大的才是。不论Anne到底是个法国人还是个华人,我都觉得,她其实并没有「被自己吓到」,这一段,显得有点「不够真实」。

至于其他技术性层面,暗场太过频繁,换场速度却不够快,造成情绪中断,也让Andre的异想世界显得不够混乱。寿臣的场地,配上这次的布景,我真心觉得,两边的观众席应该直接标上「partial view」,毕竟,看不到布景默默地彻走厨房里的家俱,确实是已经影响到整体观赏感了。至于背景音乐,印象不是很深了,但第一场,我一直觉得那个低音断在非常奇怪的地方,感觉像是播放一个loop然后,不小心要回头重播时没有接上。(第二场没有这种感觉,但也没印象听到那个低音,所以我真的忍不住怀疑这是不是技术性失误?)
不小心又写太长在此打住。以下,为不专业观众之散场奇想:
#彭杏英小姐,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太早退休,就算不常站在舞台上,也请努力维持生理和心理的巅峰状态。我是真心觉得,假以时日,你非常有潜力成为一个,只要站在台上,不用说话就能抓住观众所有专注力的神级演员,请不要让观众遗憾!
#如果哪一天,当Anne对着观众说话时,我脑子浮现的对白不是「妈妈好凶」,而是只想冲上台抱住她的话,你就成功了!(到底是为什么从龙袍到父亲,我都没办法克服「妈妈好凶」障碍?)
#Anne的红色洋装裙摆好漂亮(这楼歪太大了)!
#暗黑版Pierre那两巴真的打太小力,比较像在玩吧!
#寿臣剧场的工作人员可以不要在演出时走来走去吗?我知道你有责任在身,但你一直走来走去也是会影响我看戏的!
#期待Rerun,真心的!
图片来源:香港话剧团Facebook
转载请注明源自 每日美剧 www.meirimeij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