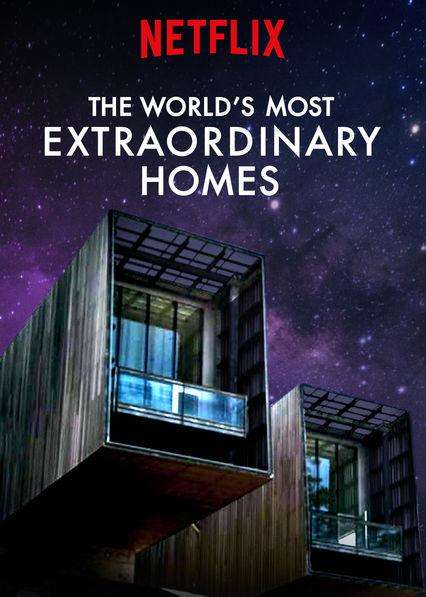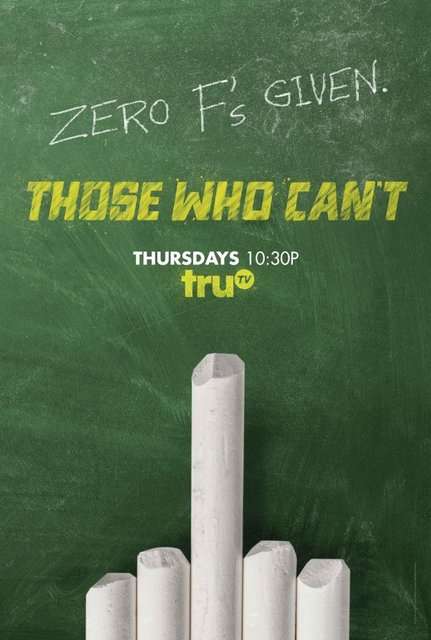浮生钓手
蔡 玮 发布于 2017-05-08
奇戈契˙欧比奥马Chigozie Obioma《浮生钓手The Fishermen》(2015)[小说阅心] [有雷]
撰文/蔡玮
每一章都用一名物做标题、明喻主要人物,予人一种部落口传文学的印象、兴味。全书透过一名奈及利亚少年的观点,娓娓叙述一桩惊恐的复仇故事、谋杀事件的始末。主人翁及其兄弟,以钓手为荣,那条让少年兄弟充满丰收想像的大河-欧米阿拉河,其实已经成为故乡阿库雷一个充满诅咒、死亡、污秽不堪的存在。大河既是历史,又是母亲与血源的呼唤。在依博族的传统里,巨莽正因为被视为河神的化身,受到如同圣牛在印度教徒之间同等的礼遇。钓手立于水面与陆地的中介,正是造意者对自身处境的自况。少年刑满出狱,外面的世界早已经起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文人政府与经济发展,悄悄的取代了军人威权统治与对部落习俗的敬畏。而原来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做为一暧昧的存在的社区,则是彻底的消失无踪。
主人翁及一起犯案的兄弟,犹如莎翁笔下的丹麦王子。对于阿布鲁的预言的犹豫不决,未能在第一时间采取断然拒绝接受的态度,结果就是付出额外高昂的代价。阿布鲁的原型,似乎脱胎于依博族传统追悼仪式上出见的伊古古。后者由一名长老穿戴代表祖先的面具,以后者的身分出现在祖灵屋,其浑身散发着象征死亡的腐尸恶臭,横冲直撞挥刀向人群,鼓励人们复仇雪恨,俨然纯粹的愤怒、暴力的冲动的化身(《分崩离析》)。但阿布鲁又是因为弑兄、性侵自己的亲人,成为传统习俗意义上的被隔离者、放逐者。他是大地女神的亵渎者,理应死后尸体被排斥在土地之外,由外族处理后事。在故事中,却死在同族的主人翁兄弟之手。杀害同族,同样犯了亵渎女神的禁忌。阿布鲁的下场,死后尸体还给了家乡的母亲河。杀害他的主人翁兄弟,一个远走他乡,一个接受了现代法庭的判刑。因崇拜依博族传统英雄欧康阔的三哥,犯下杀人罪之后逃亡、最后失去音讯,他在少年出狱后,只隐约的如鬼魂般出现在自家的后院。他代表的是欧康阔与传统习俗在少年心理上的退位,但他未真正的离去。就像主人翁以钓手自居,立于水陆两个世界之间,一如他实际存在于部落与当代的社区两个不同的宇宙之间。何况,阿布鲁死于钓手用钓竿制作的武器戳刺。他不死于过去习俗定义的敌人,而死于同族与处于夹缝的暧昧空间的尴尬者之手。
阿布鲁的弑兄娶母,让人想到希腊悲剧的依底帕斯王的故事。他触犯人伦的禁忌,象征性的让他回到自己生命的源头,又让自己永远成为被隔离在做为人的范畴之外的存在。对阿布鲁而言,前者让他具备了透视死亡的预知能力,后者则让他成为现实社会中最令人不齿、畏惧的无赖、流浪汉。(被放逐者,依博人称做欧苏,意思是献给神祇的人,他们聚集在靠近大神坛的一个特定地区,与村落隔离,他们被禁止与村民通婚,他们的标记是一头捲曲的长发,欧苏一生忌讳剃刀,因为如果他们剃去长发,神祇就会令彼等丧命,《分崩离析》,第十八章)
严格的说,阿布鲁正是在少年潜意识中传统的化身。无形中选择了接受现代的法律的制裁,也正代表了主人翁班杰明与选择传统的三哥欧班比正式的分道扬镳。何况,阿布鲁当初预言亚古家的大哥将死于钓手之下,日后造成大哥依卡纳与二哥哈波兄弟相残,却也无意间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彷彿是以寓言故事的情节,说明过去奈及利亚之所以陷入内战,以及传统自动在人群心中消失的原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崩离析》(奇努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1958)里,教士尚且按照宗教义理,无差别的对待传统中的遭放逐者(他们一走进牧班塔的教会,已经在里面的村民立刻自动避开,牧师凯亚葛说服信众接纳欧苏,但命令欧苏剃头,作为弃绝部落宗教的表征,同前书)。但在本书中的故事里,却安排阿布鲁因为出现在主人翁两位长兄的告别式的教会仪式上,遭到少年父亲私下严厉的报复。父亲并因为复仇的失败,导致一目失明。这种一眼无法望穿、无法顺利分派的意识形态利益的暧昧,正好说明了造意者经营书写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必须维持平衡,又不得不传递必要信息的苦涩心境、与用心。(20170505浮生钓手)
*浮生钓手/奇戈契˙欧比奥马着,陈佳琳翻译。台北市。大块文化,2016年
撰文/蔡玮
每一章都用一名物做标题、明喻主要人物,予人一种部落口传文学的印象、兴味。全书透过一名奈及利亚少年的观点,娓娓叙述一桩惊恐的复仇故事、谋杀事件的始末。主人翁及其兄弟,以钓手为荣,那条让少年兄弟充满丰收想像的大河-欧米阿拉河,其实已经成为故乡阿库雷一个充满诅咒、死亡、污秽不堪的存在。大河既是历史,又是母亲与血源的呼唤。在依博族的传统里,巨莽正因为被视为河神的化身,受到如同圣牛在印度教徒之间同等的礼遇。钓手立于水面与陆地的中介,正是造意者对自身处境的自况。少年刑满出狱,外面的世界早已经起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文人政府与经济发展,悄悄的取代了军人威权统治与对部落习俗的敬畏。而原来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做为一暧昧的存在的社区,则是彻底的消失无踪。
主人翁及一起犯案的兄弟,犹如莎翁笔下的丹麦王子。对于阿布鲁的预言的犹豫不决,未能在第一时间采取断然拒绝接受的态度,结果就是付出额外高昂的代价。阿布鲁的原型,似乎脱胎于依博族传统追悼仪式上出见的伊古古。后者由一名长老穿戴代表祖先的面具,以后者的身分出现在祖灵屋,其浑身散发着象征死亡的腐尸恶臭,横冲直撞挥刀向人群,鼓励人们复仇雪恨,俨然纯粹的愤怒、暴力的冲动的化身(《分崩离析》)。但阿布鲁又是因为弑兄、性侵自己的亲人,成为传统习俗意义上的被隔离者、放逐者。他是大地女神的亵渎者,理应死后尸体被排斥在土地之外,由外族处理后事。在故事中,却死在同族的主人翁兄弟之手。杀害同族,同样犯了亵渎女神的禁忌。阿布鲁的下场,死后尸体还给了家乡的母亲河。杀害他的主人翁兄弟,一个远走他乡,一个接受了现代法庭的判刑。因崇拜依博族传统英雄欧康阔的三哥,犯下杀人罪之后逃亡、最后失去音讯,他在少年出狱后,只隐约的如鬼魂般出现在自家的后院。他代表的是欧康阔与传统习俗在少年心理上的退位,但他未真正的离去。就像主人翁以钓手自居,立于水陆两个世界之间,一如他实际存在于部落与当代的社区两个不同的宇宙之间。何况,阿布鲁死于钓手用钓竿制作的武器戳刺。他不死于过去习俗定义的敌人,而死于同族与处于夹缝的暧昧空间的尴尬者之手。
阿布鲁的弑兄娶母,让人想到希腊悲剧的依底帕斯王的故事。他触犯人伦的禁忌,象征性的让他回到自己生命的源头,又让自己永远成为被隔离在做为人的范畴之外的存在。对阿布鲁而言,前者让他具备了透视死亡的预知能力,后者则让他成为现实社会中最令人不齿、畏惧的无赖、流浪汉。(被放逐者,依博人称做欧苏,意思是献给神祇的人,他们聚集在靠近大神坛的一个特定地区,与村落隔离,他们被禁止与村民通婚,他们的标记是一头捲曲的长发,欧苏一生忌讳剃刀,因为如果他们剃去长发,神祇就会令彼等丧命,《分崩离析》,第十八章)
严格的说,阿布鲁正是在少年潜意识中传统的化身。无形中选择了接受现代的法律的制裁,也正代表了主人翁班杰明与选择传统的三哥欧班比正式的分道扬镳。何况,阿布鲁当初预言亚古家的大哥将死于钓手之下,日后造成大哥依卡纳与二哥哈波兄弟相残,却也无意间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彷彿是以寓言故事的情节,说明过去奈及利亚之所以陷入内战,以及传统自动在人群心中消失的原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崩离析》(奇努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1958)里,教士尚且按照宗教义理,无差别的对待传统中的遭放逐者(他们一走进牧班塔的教会,已经在里面的村民立刻自动避开,牧师凯亚葛说服信众接纳欧苏,但命令欧苏剃头,作为弃绝部落宗教的表征,同前书)。但在本书中的故事里,却安排阿布鲁因为出现在主人翁两位长兄的告别式的教会仪式上,遭到少年父亲私下严厉的报复。父亲并因为复仇的失败,导致一目失明。这种一眼无法望穿、无法顺利分派的意识形态利益的暧昧,正好说明了造意者经营书写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必须维持平衡,又不得不传递必要信息的苦涩心境、与用心。(20170505浮生钓手)
*浮生钓手/奇戈契˙欧比奥马着,陈佳琳翻译。台北市。大块文化,2016年
转载请注明源自 每日美剧 www.meirimeiju.com